|
在山东省菏泽市的牡丹区和曹县交界处,有三个相距不过一二里路、形成“品”字形的村庄,分别叫刘岗、曹楼和伊庄。三村是抗战时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因日军经常在地图上用红笔把三村圈在一起,并写上一个大大的“赤”字,为此人们称之为“红三村”。1940年10月至1941年初,在9000多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包围及进攻下,我少量地方武装和三村群众顽强保卫“红三村”3个月,并取得最后胜利,“红三村”从此闻名天下,并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赞扬。 大敌当前,地委决定坚守“红三村” 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领一个营,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重镇菏泽,在曹县西北的刘岗一带联合地方抗日武装,组建了冀鲁豫边区支队,开辟了以菏泽、曹县为中心的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刘岗、曹楼、伊庄三村和附近的安陵是鲁西南根据地的首府,鲁西南地委和军分区在这里领导着百万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1940年8月4日,杨得志率冀鲁豫边区支队主力奉命返回黄河以北参加反“扫荡”作战,原陇海支队一、二大队随行,鲁西南地区仅留下地委机关和军分区独立团团长张耀汉带领的一支200多人的武装在这一带坚持斗争。 鲁西南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是八路军控制陇海路的一个前沿阵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八路军主力部队北上后,盘踞在鲁西南的国民党顽军趁机猖獗起来,分六路从四面八方大举进攻以“红三村”和安陵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中共鲁西南地委机关及抗日武装。这六路顽军分别是:北面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张志刚部2000余人,西面考城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九支队胡金泉部2000余人,东南面国民党曹县保安旅旅长王子魁及其所辖石福启部1000余人,西南面国民党苏鲁豫挺进军第八纵队司令张胜泰部1000余人,以及尾随其后的第十二纵队司令马逢乐部1000余人,还有国民党定陶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王子杰部近1000人,总兵力达到9000余人。 当时,鲁西南地委将鲁西南地区的中心区分别划为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内有100余个村庄;第二道防线内有20余个村庄;万一前两道防线坚守不住,就只有固守第三道防线,即由“红三村”构成的防线。为了固守第一道防线,地委派王法礼带领游击小组和民兵共10多人,驻守南边的沙扈村。9月的一天晚上,国民党曹县保安旅旅长王子魁率部将沙扈村团团包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王法礼和战友们最终全部牺牲。第一道防线失守后,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各路顽军纷纷向我中心区进逼,并得意忘形地叫嚣:“红三村成了孤岛,不用两天就把它淹没了!”“共产党鲁西南根据地,如今一枪就能打穿,红三村就要完蛋了!”“共产党的老窝已不堪一击,在红三村召开祝捷大会指日可待!” 地委接受了分散驻守即第一道防线失利的教训,决定第二道防线不再分兵驻守,而是依靠当地民兵和群众骚扰、牵制顽军,尽量保存力量,紧缩拳头,重点固守“红三村”。 由于形势愈来愈严峻,1940年9月15日,鲁西南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地委书记戴晓东严肃地对大家说:“眼下局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应该怎么办?请大家谈谈看法。” 戴晓东话音刚落,有的同志就抢先发表了意见:“把武装拉走,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待主力回来再公开活动。” 这位同志的意见遭到多数同志的反对,大家认为,本来八路军主力北上对群众坚持斗争的情绪就有所影响,如果再把留下的这点武装拉走,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就会更加动摇群众的斗争信心。我们必须坚持公开斗争,而且也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地委还在,有党的领导;有一支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200多人的武装;“红三村”的广大群众有着坚定的斗争信心和丰富的斗争经验;还有周围数十村的支援。顽军虽有数十倍于我的兵力,但他们来自两省五县,分属不同派系,各有各的地盘和目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一个人能统一起来,且出师不义,士气低落,大有可乘之机。只要我们审时度势,正确领导,就能将斗争公开坚持下去。 戴晓东听了大家的发言,见大家已经形成共识,就坚定地说:“好,就这么定了!红三村的存亡,关系着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存亡。我们一定要坚持到主力打回来!” 尔后,地委进行了战斗分工:地委书记戴晓东和宣传部部长袁复荣率领地委机关大部分人驻伊庄,有枪10余支,负责指挥全局;组织部部长王健民率机关少数人驻刘岗,领导群众保卫刘岗,并支援其他两村的斗争;军事部部长宋励华率领十余名武装人员和曹县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驻曹楼,主要任务是打击镇压地方上的坏分子,扰乱和打击小股顽军,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敌情;统战部部长刘齐滨带病驻井王村,以其在鲁西南的威望,广泛利用关系进行统战工作;由张耀汉带领军分区独立团,作为机动力量,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法,寻机歼敌,牵制顽军力量。 众志成城,军民痛击各路来犯之敌 一听说地委决定坚守“红三村”,“红三村”内立刻群情振奋,誓死保卫红色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红三村”每村都成立了战斗指挥部,青壮年男子组成战斗队,妇女和儿童团组成后勤队,身体稍好的老年人也主动报名参加守寨队、巡逻队或后勤队。当时的“红三村”,人人皆兵,大家听从指挥部的统一指挥。战斗队行动军事化,集中住宿,日夜站岗放哨。土枪、土炮、长矛、铁锨、斧头都成了队员们的武器。三村中的富裕户,也积极支持保卫“红三村”的斗争,有的主动捐出粮食、棉花、衣服、布匹。 为利于固守,“红三村”群众将旧寨壕开挖一丈多深,从寨内挖有暗道与寨壕相通,以便出击,三个村之间也都挖有交通沟。三村都加高增厚了寨墙,寨墙上置有土枪、土炮、长矛和砖石瓦块,墙垛上备有滚木和礌石,寨墙上每隔二三十步远就悬挂一个上面带罩的灯笼,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下边却看不到寨上,寨墙上白天每50步一人、夜里每10步一人站岗放哨。干部和群众一起值夜班,地委的几个领导同志每夜都巡逻几趟。同时,地委几名负责人还分别带领部分武装深入“红三村”及外围部分村庄,放手发动群众。众志成城的“红三村”军民,誓与“红三村”共存亡。 一切准备停当,一场顽强、巧妙的斗争就此展开了。 1940年10月下旬,进驻到伊庄对面的顽军王子魁部,凭借一门迫击炮,率部向伊庄进犯。凌晨时分,战斗打响了。当敌人突击队逼近寨墙时,墙上军民立即推下滚木,把云梯上的敌人砸了下去,又用手榴弹和石头向敌群猛砸,将敌人突击队消灭在寨墙下。敌人又调动大部队继续攻寨,伊庄军民毫不畏惧,猛烈还击。这时,驻守曹楼、刘岗的军民按照事前“一村有情况,各村齐支援”的约定,从背后侧翼向敌人发起攻击,张耀汉带领军分区独立团的200名战士也及时赶来投入战斗,敌人腹背受挫,仓惶逃窜。这是保卫“红三村”的第一仗,这次战斗的胜利,使“红三村”得到武器和弹药补充,打击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嚣张气焰,对处于抗日战争艰难岁月的鲁西南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 11月中旬,王子魁令其部下兵分两路向曹楼进攻,遭到守寨军民的顽强反击。顽军被杀伤一部分后,恼羞成怒,在火力掩护下将寨壕填平一段,爬上寨墙。守寨军民用土枪、土炮、砖石瓦块打击顽军,将顽军压回寨外。正在这时,军分区独立团赶来从后侧包抄顽军,顽军在内外夹击下仓皇逃窜。败退的顽军又遭到从刘岗、伊庄赶来的民兵的截击。三个村的男女老少个个手舞大刀、长矛前来助战,共击毙顽军40余名,缴枪21支。“红三村”军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短期内两胜顽军,大大鼓舞了斗志,更加坚定了固守“红三村”的信心。 1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情报员王大爷跑到守寨总指挥部反映说:“俺邻居到南面的村子走亲戚,听说鬼子明天要攻打我们红三村,咱们得早做准备啊!”确认情报真实后,总指挥部立即召开“红三村”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后制定了“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的作战方针。 第二天夜里,在汉奸伪区长芦朗斋的带领下,20个日寇和200多伪军直扑“红三村”。地委决定改变过去硬碰硬的打法,把敌人放进来,关门打狗。当时,“红三村”的十二个寨门大开,民兵们手持长矛、大刀,埋伏在沿街、巷口的围墙里严阵以待。拂晓时,随着远处的狗叫声和零星的枪声,敌人闯进了曹楼村,敌人一看寨门大开,以为人都跑光了,就毫无顾忌地进村烧房。当他们行至村中心时,随着党支部书记李修生的一声令下,房上、墙头的枪炮声顿时响作一片,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健民亲率刘岗军民及时赶来增援。敌人见势不妙,不敢恋战,急向伊庄方向逃窜,又陷入伊庄民兵的埋伏圈。敌人处处挨打,不敢停脚,丢下大批的死尸和枪支弹药,大败而回。“红三村”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随着敌人对“红三村”屡次进攻的失败,其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日益尖锐。顽军们虽然都想抢占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地盘,但是除王子魁一股外,其他几股顽军想的更多的还是如何保存实力,进攻“红三村”的劲头不那么高了,这就给“红三村”下一步进行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时机。 各个击破,三村迎来最后的胜利 敌人对“红三村”多次进攻未果,便改变战术,实行层层封锁,把“红三村”团团包围起来,力图把三村军民困死、饿死。地委决定派一些干部插到敌占区,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抗粮抗捐,开展“反资敌”运动,以拖住敌人后腿,减轻三村的压力。 首先吃到我空室清野苦头的是北边进驻菏泽、曹县两县共管的安陵集村的孙秉贤和张志刚。当时时近初冬,天气渐冷,孙、张部贴出征粮索衣的布告,没人去看;挨家翻箱倒柜,也是空空如也;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向导,两眼漆黑,经常遭到我游击小组的伏击。不几天,顽军又冻又饿,狼狈至极。老百姓见了心中大快,趁势放出风声说:“红三村的八路军在绑梯子,要攻打安陵集啦!”“杨得志的队伍从北边开回来了!”张志刚听了吓破胆,像《空城计》中的司马懿一样,急忙命令他的喽啰“后退40里安营扎寨”,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三村北面的威胁解除了,可是西面的“反资敌”工作却做不下去了,因为遭到地主武装红枪会的阻挠和破坏,并且杀害了我方“反资敌”工作骨干。这个红枪会的头子和顽军头领马逢乐有勾结,又是日寇的忠实走狗。一天夜里,地委军事部部长宋励华得到消息,说那个红枪会头子正在一个村庄看戏。宋励华就带着几个便衣战士假装看戏赶到那个村庄,将那个红枪会头子当场活捉,并大声向周围的群众讲道:“乡亲们,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给你们撑腰,放心大胆地干吧!坚决不给敌人一颗粮食、一两棉花,饿死他们、冻死他们!今天我代表三村法庭,依法判处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死刑!”群众一听说八路来了,高兴万分,喊起了口号。口号声中,一枪结束了这个红枪会头子的命。 “红三村”西北二十里的毕寨伪区长周花脸听说这件事后,发誓要给土八路点厉害尝尝。他带了几个亲信去找顽军,策划血洗“红三村”,途中夜宿周家集。宋励华得到消息,骑上马连夜赶到周家集,把周花脸和几个汉奸堵在被窝里用枪“点了名”。这样,宋励华他们骑着快马,在西部神出鬼没地穿来穿去,镇压了一批汉奸顽匪,打下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反资敌”斗争又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西边的顽军头目马逢乐得不到粮食和布匹,日子很不好过,就想勾结另一个顽军头目胡金泉攻打三村。胡金泉原来是一股势力很大的土匪头目,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当了独立旅旅长。这支部队有2000多人,装备精良,轻重机枪有100多挺。由于我方发动了“反资敌”斗争,他们同样也是没吃没穿。同时,我方了解到他与马逢乐有旧仇,对攻打三村有些迟疑不决。地委决定对胡金泉开展统战工作,尽力把他争取过来。 戴晓东通过关系,主动找胡金泉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的方针政策,谈得很投机。戴晓东有个六岁的小女儿,胡金泉为了与八路搞好关系,为自已留条退路,主动提出要认干女儿。考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有利于革命斗争,戴晓东满口答应了。胡金泉见八路军如此讲情义,十分高兴,发誓保持中立。后来他与我军的关系一直比较好,还悄悄卖给我军子弹,许多伪顽军多次要求他攻打三村,都遭到他的拒绝。“反资敌”斗争和统战工作的开展,对减轻“红三村”的压力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冬季,“红三村”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粮食眼看要吃光了,严冬腊月战士还没弄上棉衣。共产党员、农会会员勒紧腰带,地委领导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忍饥挨饿拿出一些吃的分给三村群众。在那守卫三村的日日夜夜里,大家每天只能喝碗玉米糊糊。尽管天寒地冻、饥寒交加、大兵压境,英勇无畏的三村军民毫不气馁,他们决心与三村共存亡。三村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地委于11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戴晓东赴河北向八路军主力汇报,请求支援。同时,号召三村军民团结一致,树立必胜信念,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940年12月,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的杨得志听了鲁西南地委的汇报后,当即派出主力部队日夜兼程赶往“红三村”。31日,八路军主力部队赶到鲁西南后连续向敌人发起攻击,在常乐集一带消灭王子魁部300余人,继而又歼灭石福起部600余人,其他几股顽匪望风而逃。就这样,长达3个月的“红三村”保卫战终于胜利结束。 “红三村”保卫战的胜利,创造了平原地区坚守根据地的范例,从此闻名天下。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专门写出报告上报中央,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做了《鲁西南三个村庄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讲话,作为反封锁、反“蚕食”斗争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全边区推广。杨得志也在给“红三村”军民的亲笔嘉奖信中称赞道:“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心里。” (责任编辑:lsly) |
当前位置: > 烽火硝烟 >
抗日传奇“红三村”
时间:2016-05-23 10:05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admin 点击:
次
在山东省菏泽市的牡丹区和曹县交界处,有三个相距不过一二里路、形成“品”字形的村庄,分别叫刘岗、曹楼和伊庄。三村是抗战时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因日军经常在地图上用红笔把三村圈在一起,并写上一个大大的“赤”字,为此人们称之为“红三村”。1
顶一下
(29)
10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 单位名称:菏泽市烈士陵园
- 地 址: 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刘寨村北100米路东
- 邮政编码:27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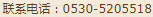
- 推荐内容
-
